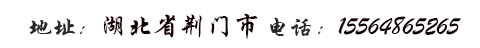叶芝对我的创作的总介绍
|
白癜风趁早治疗 http://pf.39.net/bdflx/131204/4302820.html 对我的创作的总介绍 文/叶芝 一、首要原则诗人在他的以生活的悲剧为素材的最佳作品中总要写他个人的生活,无论是怎样的生活,悔恨,失恋或纯粹的孤独。他从不对什么人直言,就象在早餐桌上与某人交谈那样,在他那里总是存在着变幻不定的场面。但丁和弥尔顿写神话传说,莎士比亚则写英国历史或传统骑士故事中的人物。诗人从来就不是那个偶然的、缺乏条理的、坐在那儿用早餐的人,甚至当他看起来与本人最相像的时候,无论当他是雷利,当着君王的面撒谎的时候,还是雪莱,“一根神经上蠕动着人世间那些感觉不到的压迫”的时候,或是拜伦,正如“利剑刺破剑鞘”,“灵魂磨穿了胸膛”的时候,他已再生为一种思想,某种意料中的完美之物。小说家或许可以描写自己偶然的经历,他的那些支离破碎的事件,但诗人却不可以。他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典型,与其说是典型不如说是激情。他是李尔王、罗密欧、俄底浦斯、蒂利希阿斯①;他是戏剧中的人物,甚至他所热恋的女人也是罗莎琳②,克娄巴特拉,而绝不是黑夫人③。他是他自身经历的幻觉场景的一部分。我们敬重他,因为自然变得明白易解了,而且如此它也变成了我们的创造力的一部分。《六问奥义书》④说:“当心迷失于自性的光辉中时,它不再梦想;它仍然存在于肉体之中,但却迷失于幸福之中。”《唱赞奥义书》说“智者在‘自性’中寻觅那些活着的或死去的人,去求取这个世界所不能给予的东西。”天地无所知,因为它们不创造任何东西,我们无所不知,因为我们创造了一切。二、题材正是通过芬尼亚运动老领导人约翰·欧李尔瑞⑤,我才找到了我的创作主题。他长期的铁窗生涯,他的为期更长的流放生涯,他的出众的才智,他的学识,他的自尊,他的正直,一个在小商店和小农场里孕育起来的完美的贵族,吸引了一群年轻人来到他的身边。我当时年仅十八九岁,在《仙后》和《悲伤的牧羊人》的影响下,已经创作了一部田园剧,在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影响下,我写了两个剧本,一个适合在高加索山脉的某地上演,另一适合在月球的火山口演出。我知道我的思想既不明确又缺乏条理。他给我看托马斯·戴维斯⑥的诗歌,说它们并非什么好诗,但在他年轻的时候却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谈到了与戴维斯交往的其他诗人和《民族报》,大概还借给我一些他们的诗集。它们不是什么好诗,这一点我甚至比欧李尔瑞看得更清楚。我只读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厌恶18世纪那种干巴巴的修辞学书。但是,这些诗人具有一种我过去赞赏现在仍然赞赏的品质:他们并不是各不相干的个人,他们代表某一个民族或试图代表某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讲话,在他们的身后还延续着世世代代。尽管只是偶然地,就象年轻人了解事情那样,我知道我应该厌恶那种被乔纳森·斯威夫特比喻为蜘蛛从肚子中抽丝所结的网的现代文学。我过去憎恨观点文学,而现在仍以与日俱增的厌恶憎恨它。假如我的无知允许的话,我要寻回荷马,还有那些与他同桌宴饮的人们。我要象所有的人那样大声哭泣,象所有的人那样开怀大笑,“青年爱尔兰”诗人们在不写纯政治性文章时也有同样的愿望。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研究公众和适合他们的语言需要耗费毕生的精力,而一旦研究出来却可能得不到普遍的认可。后来,有人,不是欧李尔瑞,向我谈起斯坦迪什·欧格莱蒂⑦和他对爱尔兰神话传说的诠释。欧李尔瑞还把我介绍给欧卡瑞⑧,可是我的那种孩子气的惰性使我无法承受他那未经整理和解释的历史学著作。在《民族报》创刊的前一代,爱尔兰皇家学术院就开始了对爱尔兰古代文学的研究。此项研究是创建议会的新教贵族的礼物,同样也是《民族报》及其学派的礼物,尽管戴维斯和米切尔⑨是新教徒;它也是天主教中产阶级的礼物,他们当时正在筹建爱尔兰自由邦。学术院说服英国政府出资赞助一项大规模的调查,以便绘制一份英国和爱尔兰的正式地图。学者们,包括那个大学者欧多诺凡⑩,被派去挨个走访所有的村庄,记录下村庄的名称和它们的神话传说。也许这是此类工作能够圆满完成的最后一个机会了,人们的记忆还完好无损,采集者本人也许听到过报丧女妖(11)的声音或亲眼见过报丧女妖;爱尔兰皇家学术院及其大众读者以同样的热情欢迎异教徒和基督徒;认为圆形塔楼是波斯拜火教的纪念物。极少有正统派感到吃惊;天主教徒被打垮吓倒了。我的一个受人尊敬的叔祖——某位被遗忘的大师为他绘制的肖像画现在还挂在我卧室的墙上——一个爱尔兰教区长,有时会夸口说他能绝对恰当地用读神的或下流的言语来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有些县在被调查之后却没有什么东西出版,英国政府唯恐激起危险的爱国主义情绪,撤回了赞助。大量的手稿还留待出版,其中包括学者间许多生动有趣的来往信件。在爱尔兰现代文学的发展初期,欧格莱蒂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他能以令我们不敢苟同的狂言让我们高兴起来;他说,总有一天,斯利夫一那一蒙山会比奥林匹斯山更著名。然而他绝不是一位我们根据字义所理解的那种民族自治论者,就象他喜欢解释的那样,他反对的是众议院而不是国王。他的堂兄,海伊斯·欧格莱蒂(12),不愿加入我们的非政治性团体——爱尔兰文学社,因为他认为该社是一个芬尼亚运动组织。可是他自夸说,尽管他在英国生活了40年,他却从未与任何英国人交过朋友。他在大英博物馆工作,负责编辑他们的盖尔语书目,并且以18世纪的狂热翻译我们的英雄传奇故事;他的女主人公“心破碎了”,他的男主人公“登上高高的山顶”,在那儿“挥动他的标枪”,而随后乘船航行在“广阔无垠的海面上”。欧格莱蒂兄弟把自己看作旧爱尔兰土地贵族的代表;他们也许,斯坦迪什·欧格莱蒂肯定,认为英国,因为颓败和民主,已经背叛了他们的秩序。也正是那个秩序里的另一成员,格雷戈里夫人(13),要为《诸神和战斗的人们》和《缪尔辛姆呐的库胡林》中的英雄传说做夏洛特·盖斯特夫人(14)的《麦比诺吉恩》为威尔士英雄传说做过的事情,而后者在美感和风格上都较为逊色。斯坦迪什·欧格莱蒂具有很强的现代观念,他的风格,如40年前约翰·米切尔的风格一样,是受卡莱尔的影响而形成的。格雷戈里夫人则在她周围的盎格鲁—爱尔兰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是一种古老而生动的方言,带有部分英国都锋王朝时代的词汇,部分句式是由仍用盖尔语思维的人们规定的。在斯来沟的农舍里或从罗西斯岬角(15)的水手那里,我曾听到过无数鬼怪的故事,无论是关于新近过世的还是历史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或是那位梅娃女王(16),她的久负盛名的石家就立在海湾对面的山上。后来我在大英博物馆读到了40和50年代爱尔兰作家写的这类鬼怪故事,但它们不仅没让我感到满意,反而激怒了我,因为它们把这个国家的梦想变成了笑话。但是,当我和格雷戈里夫人挨家挨户走访农舍,看着她记录她那本题为《幻景与信仰》的杰出集子的手时,我避免毁损幽默。在整个爱尔兰历史的背后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壁毯,甚至连基督教也不得不接受它,并且置身其中。看着它模糊的褶痕,没人能说出哪儿是基督教的起源,哪儿是巫术祭仪的终结;“在飞禽中有一完美者,在鱼类中有一完美者,在人类中也有一完美者”。我只能以近代学者的那种观点来解释——剑桥的柏基特教授(17)的推荐使我注意到它——圣·帕垂克(18)来到爱尔兰的时间不是5世纪,而是接近2世纪末。大论战还没有开始;复活节仍然是春分后第一次月圆之后的星期日。在混沌初开的一日,诺亚方舟停留在亚拉腊山上,摩西带领古代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联系着基督教和古代世界的脐带尚未剪断,基督还是狄俄尼索斯的异母兄弟。刚刚被督伊德祭司们剃度的人会从最近的基督徒邻居那儿学会在自己身上画十字,却丝毫没有感到不协调。他的孩子们也不会有那种感觉。有组织的氏族削弱了教会组织,他们能够接受僧人但却拒绝接受主教。一个现代人,脑子里装着《金枝》(19)和《人的个性》(20),在圣·帕垂克的“教义”里找到了许多共同的思想感情,“教义”记载在他的《忏悔录》中。除了基督不久将审判生者和死者的声明中“不久”一词以外,其它内容都是可以接受的。他会重复它,甚至相信它,而丝毫不考虑历史上的基督,或古代的犹大,或任何依照历史猜测和不可靠证据考证出来的事情。我重复它,想起了《奥义书》中的“自性”。在后来的岁月里,这种传统,口头的或文字记载的,又增加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片断,犹太神秘哲学的词语——我在多纳瑞尔(21)曾听到过“tetragrammatonagla”(22)这样的词语——中世纪思想的浮游碎片,但不是任何使孤独的心灵反感的东西。甚至与巴洛克艺术和洛可可艺术相对应的宗教学说都不能作为思想而为我们所接受,这可能是由于盖尔语不具备抽象思维能力。它以残酷的面目出现。在现代爱尔兰文学的诞生之际,那块壁毯就充满了这个场景,它存在于《众圣之井》的作者辛格(23)的作品中,在詹姆斯·史蒂文斯(24)的作品中,在格雷戈里夫人的全部作品中,在乔治·拉塞尔(25)的所有与《奥义书》无关的作品中,存在于我的除后期诗歌之外所有的作品中。有时我听说,我所领导的运动是在年行刑队的镇压下走向衰亡的,如果说这话的报纸属于爱尔兰,那就是赞扬,如果属于英国,那则是谴责;有时人们又说,那些行刑队使我们的现实主义运动成为可能。即使这种说法正确,那也只是对了一部分,传奇故事在各地正走向衰亡,因为在皮尔斯(26)和他的战友的想象中,“大众的献祭”在这壁毯里找到了红枝英雄(27)。他们走出去赴死,召唤着库胡林(28):赫克里斯,在暴风雨中从天国降临来清扫人世这个肮脏的牛棚吧。从某种意义上讲,年的诗人并不象报界所声称的那样属于我的这个流派。现代天主教教义的普及起源于蜘蛛抱蛋,而非出自那西(29)的子孙,它使盖尔同盟的人羞怯退缩。他们畏惧凭理智行事的大胆精神,一味拘泥于字典和语法。皮尔斯和麦克唐纳(30)以及其他被枪决的人一定会用盖尔语做或者试图去做我们用英语做过或试图去做的事情。我们的神话,我们的传奇故事,和其它欧洲国家的不同,因为直到17世纪末他们一直都注重,或许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农民和贵族的平等;荷马是属于那种长时间伏案工作的人,甚至在今天,我们古代的王后、我们中世纪的士兵和情侣们都能使一个商贩不寒而栗。我能让我自己的思想,那种或许是在用古代哲学研究现代环境时所感到的绝望,借17世纪漫游诗人,或想象中的某一位现代民谣歌手之口表达出来。我的思想越深刻,民谣歌手和漫游诗人就越真实可信,越象农民。一些现代诗人主张爵士乐和音乐厅歌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间艺术,我们应该以它们为原型来塑造我们的艺术;我们爱尔兰诗人,同样是现代人,不接受任何不能追溯到奥林匹斯山的民间艺术。给我时间和一点青春,我会证明甚至象“约翰尼,我几乎不认识你”这样的话也能追溯到奥林匹斯山。在《历史研究》一书第2卷的附录中,阿诺德·汤因比(31)先生描述了他所谓的泰西基督教文化的诞生和消亡;它在惠特比的西诺德失去了称霸欧洲的机会,在12世纪,由于“爱尔兰基督教界自始至终拒绝并入罗马教会”,它在教会方面遭到了最终的失败。“在政治和文学领域”,泰西基督教文化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到17世纪。他还坚持认为假如“犹太复国主义和爱尔兰民族主义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目标的话,那么犹太人和爱尔兰人各自都会在60或70个民族共同体中找到一个小小的适当位置,”他们会感到生活多少容易一些,但不再是“一个独立社会中的遗物……古爱尔兰的骑士传奇最终完结了……现代爱尔兰已经下定决心,在我们这一代,为她自己在我们这个平凡的西方世界里找到一个作为自愿的居民的适当位置。”如果爱尔兰文学按我这一代人所构想的那样发展的话,它可能会设法保留“爱尔兰人”的生活,那就不会有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阻碍其中,就不会有他们想象的那些人物,也不会有革命回忆录里所描写的那些人物。尤其是最后这类人物,如某些伟大的前辈政治家,帕内尔(32)、斯威夫特、爱德华勋爵(33),都已经退到壁毯中去了。也许真的某些“爱尔兰人”的特点应该变得更为重要。当格雷戈里夫人请我注释她的《幻景与信仰》时,为了能理解她在盖尔威记下的那些东西,我开始研究现代招魂术。有几年我常与一些巫师交往,为了挣几个便士,那些巫师在伦敦的各个贫民区为工匠或他们的妻子指点他们与死去的亲人、与雇主以及与孩子的关系;然后我把她在盖尔威或我在伦敦的所闻与斯韦登伯格(34)的梦幻做比较,而且在我那不甚充分的注释出版之后,我又将这些所闻与印度的信仰做了比较。当我们在林间路过一位老人时,假如格雷戈里夫人不说:“那人可能知道过去的秘密”,那我永远也不会和师利·普罗希大师(35)交谈,或者请他翻译他师父的西藏游记,也不会帮助他翻译《奥义书》了。我想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库勒的猎场看守在一百年不见鹿迹的湖边听见了鹿的蹄声,为什么一个疯癫的老牧师说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人下过地狱或上过天堂,意即爱尔兰的山寨围墙把他们都圈住了;死者呆在他们生前生活过的地方,或在那附近,他们不追求抽象的乐土或地狱,而是,可以说,退到邻人隐秘的人格中去了。我深信,在两三代人之内,人们将会普遍地认识到机械的理论绝不会变成现实。自然界与超自然界是交织在一起的,为避免某种危险的狂热,我们必须研究一门新的科学。到那时,欧洲人也许会在基督身上看到某种魅力,这个基督身后的背景是巫祭而不是犹太教,不是被隔绝在僵死的历史之中,而是流动的、具体的、可感知的。我生来就带着这样的信仰,带着它生活,也将带着它死去;我的基督,我想是从圣·帕垂克的信条里得出的合理推断,是被但丁喻为比例完美的人体的那个存在统一体,是布莱克的“想象”,是《奥义书》中称为“自性”的东西;这个统一体不遥远,也并非因此是智力所能理解的。它是切近的,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它承担着痛苦和丑陋,“蝾螈的眼睛,青蛙的脚趾”。潜意识里对这个主题的专注使我写出了《幻象》,它的粗糙的几何图形是一个未完成的注释。“爱尔兰人”通过16、17世纪期间的战争保存了他们古代的“沉淀”,那些战争后来变成了灭绝人种的战争。在其《十八世纪的爱尔兰》一书的开篇,勒基(36)谈到,没有哪一个民族经历过更为惨重的迫害,直到我们自己这个时代,那种迫害仍未完全停止。没有哪一个民族象我们这样仇恨,过去的那种经历总是活跃在我们的心中。有时候仇恨在毒害着我的生命,我责怪自己柔弱无能,因为我还没有把这种仇恨充分地表达出来。仅仅把它置于一个漫游的农民诗人之口是不够的。因而我提醒自己,尽管我的婚姻是我所知的直系亲属中的第一桩英国婚姻,我家庭中所有的人都使用英国名字,我的心灵属于莎士比亚、斯宾塞和布莱克,或许还包括威廉·莫里斯,属于我用于思维、说话和写作的英语语言,我所热爱的一切都是通过英语了解的。我的恨以爱来折磨我,我的爱以恨来折磨我。我好似一个西藏僧人,在他初受灌顶之时,他幻想着他被一头野兽所吞食,而当他清醒过来时,他认识到他本人既是吞食者又被吞食。这就是爱尔兰的仇恨和孤独,这种对人生的仇恨促使斯威夫特写作了《格利佛游记》和刻在他墓碑上的墓志铭,它仍然使我们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并且怀疑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一次又一次人们问我为什么不用盖尔语写作。大约4、5年前,我应伦敦某个社团的邀请去赴一次晚宴。我发现自己处在伦敦新闻记者、印度学生和外国政治难民的包围之中。一家印度报纸说这是特为向我表示敬意而举办的晚宴;我希望这不是真的,我不记得了,尽管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自己当时愤怒的感觉。在公共晚宴上,我必须说人们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话,我必须依惯例致贺辞并接受贺辞;而后他们会谈到难民;从这时起所有人都变得活跃起来,人们开始谈论时事。外国的专制暴政会遭到谴责,甚至对那些糊涂的印度人来说,英国似乎也算是自由的庇护者。我的愤怒在不断地加剧。在埃梅特密谋起义、身亡的那一年,华滋华斯,那个典型的英国人,出版了他致弗朗索瓦·多米尼克·图桑(37),一个圣多明哥黑人的著名的十四行诗:没有一丝平凡的风会把你遗忘他对这次起义的记忆微乎其微,正象对起义前六年中的半绞刑和沥青帽的记忆一样。为了避免有关时事的演讲,我谴责了压迫印度人民的行径。作为文人而不是政治家,我诉说了他们是如何被迫以英语为工具学习一切的,甚至他们自己的梵文,直到他们的第一位智慧发现者因精于模糊抽象的思维而成为笑柄为止。我请求在座的印度作家记住,除了用母语,任何人都无法带着音乐和活力进行思考和写作。我使一群友好的听众对我充满了敌意,可是每当我想起那个情景,我仍然坚持己见,气愤不已。我不可能用盖尔语写作,正如那些印度人无法用英语写作一样;盖尔语是我的民族语言,但不是我的母语。三、风格与态度风格几乎是无意识的。我知道我试图做的事,但却不大知道我究竟做了什么事。现代的那些抒情诗,甚至那些打动了我的抒情诗——《溪流的秘密》、《多洛斯》——似乎也过于冗长,但是爱尔兰人对激流的偏爱可能仅仅是出于懒惰。然而假如彭斯阅读汤姆森(38)和考珀(39)的诗歌,他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英国人的头脑是善于思考的、丰富的、审慎的;它也许能记住泰唔士河流域。我打算写短小精悍的抒情诗或诗剧,其中的每一段话都力求简练,靠戏剧张力拼合在一起。而我这样做起来更有信心,因为年轻的英国诗人当时是出于危机时刻的情感而写作,但是他们古老的、行动迟缓的沉思,立即又恢复了,而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诗歌追随了我所开创的风格,我努力使诗的语言与热情洋溢、正常的语言相一致。我要用我们在自言自语时脱口而出的任何语言来写作,我们自言自语,我一天到晚都这样,评论着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或任何我们暂时会在其中看见自己的生活中的事件。我有时拿自己与贫民窟里那些疯癫的老妇人相比较。我听见她们在谴责、在回忆,“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见其中某一个说起某个想象中的求婚者,“瞧你这副病歪歪的样子,连个窝都没有!”如果我大声说出我的想法,她们可能也会象这样暴怒撒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创造出一种我自己喜爱的语言;大约是在20年前,我开始创造它,我发现我需要寻求的不是华滋华斯认为的那种普遍人的话语,而是一种强有力的、热情奔放的句法,是句点和诗节的完全一致。由于我需要一种热情奔放的句法来表现热情洋溢的题材,我强迫自己接受那些与英语语言同时发展起来的传统格律。埃兹拉·庞德、特纳(40)、劳伦斯(41)都能写出令人赞叹的自由体诗,但我却写不了,我会失去自我,变得郁郁寡欢,象那些疯癫的老妇人一样。当翻译者仍然在为韵律而烦恼的时候,《圣经》的译者,托马斯·布朗爵士(42),那些从事希腊语翻译的人创造了一种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形式。这种形式对非个人的冥想较为自然;而所有个人的东西倾刻问就会腐朽,应该把它包裹在寒冰或咸盐当中。有一次我染上肺炎,处于谵妄状态中,我口授了一封致乔治·莫尔(43)的信。我告诉他要吃盐,因为盐是不朽的象征。清醒之后,我对那封信已毫无印象,但我当时说那话的意思与现在的意思完全一样。如果我用自由体诗的形式,或用任何在其变格范围内保持不变的节奏来写个人的爱情或悲伤,我会在内心充满了自我轻蔑,由于我的自高自大和轻率;而且我也会预料到读者不会感兴趣。我必需选择一种传统的诗节,甚至我所做的改动也必需看起来象是传统的诗节。我把我的感情献给了牧羊人、牧牛人、赶骆驼者、学者、弥尔顿或雪莱笔下的柏拉图主义者(44)、帕尔默画的那座塔楼(45)。假如你跟我谈什么独创性,我会对你大发雷霆。我是一群人,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什么也不是。古代的盐是最上等的保鲜材料。莎士比亚的主人公们通过他们的外表神态,或通过他们内含隐喻的言谈方式,向我们传达他们视野的突然的扩展,传达他们对死亡临近的狂喜:“她从此就该离开人世了”,“千万个热吻,这是可怜的最后一个”,“让你暂时离别幸福”。他们已经变成了上帝或圣母、鹈鹕、“我怀抱里的婴儿”,但是一切都必需是冷酷无情的;没有哪一个女演员在扮演克娄巴特拉时哭泣过,甚至连浅薄的舞台监督都从未想到过这种事情。超自然的事物出现了,冷风吹过我们的手,吹拂在我们的脸上,温度下降,而且因为这样的冰冷,我们招致了新闻记者和鉴赏力低下的观众的怨恨。也许在这个或那个细节里存在着令人痛心的悲剧因素,但在整个作品里不存在任何令人痛心的悲剧因素。我曾听见格雷戈里夫人在拒绝上演寄到艾贝剧院的某个以现代手法写作的剧本时说:“悲剧对死者来说必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对抒情诗、歌曲、叙事诗来说也是一样的,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都不会因为某一作品令人痛苦而世世代代诵读传唱它。他们为其吟诵悲剧的那位侍女必须以永恒的形式从历史中提升出来,她是四位马利亚中的一个,韵律是古老而熟悉的,想象应该翩翩起舞,必须超越感情而进入到原始的寒冰中去。使用寒冰这个同准确吗?学着我父亲来信中的一句话,我曾夸口说,我要写一首“黎明般冰冷而热情的”诗。当我用无韵体写诗时。我感到很不满意;我的《女伯爵凯瑟琳》略带中古色彩,适合这样的节拍,但是用《绿盔》中的民谣调来表现我们的英雄时代却更为恰当,这也许只是我本人的见解。在我对黛尔德(46)和库胡林的看法中有某些东西抵制文艺复兴及其特有的韵律,我在舞剧中创造一种使无韵诗随着抒情诗节奏变化的形式,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我用无韵诗来表达并分析自己的感情时,我站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此时本能,及其传统的歌舞和总体上的和谐,都属于过去。我虽然已被抛出了鲸鱼腹,但我仍然记得从它的肋骨之外传来的声响和摆动。就象保罗·福特(47)的歌谣中的女王一样,我浑身散发着海鱼的腥昧。诗歌的对位结构,借用罗伯特·布里季斯(48)使用的一个术语,使过去和现在融为一体。如果我为了强调它的五音步而反复诵读《失乐园》的第一行,我就置身于民谣歌手之中——“谈到人的最初的违命和那果子”(Ofmansfírstdísobédienceandthefrúit),但是当我该朗读它时,我将它与另一种强调,热情奔放的散文的强调,交叉起来——“谈到人的最初的违命和那果子”(Ofmánsfirstdisobédienceandthefrúit)或者“谈到人的最初的违命和那果子”(Ofmánsfirstdísobedienceandthefrúit);民歌还是民歌,但是它变成了一种幽灵般的声音,一种不变的可能,一种无意识的标准。使我和我的听众为之动情的是一种生动活泼的语言,它没有任何规则,只是不能驱除这幽灵般的声音。在得到天启的那一刻,我既清醒又昏昏沉睡,在自动的屈从中不动声色;没有什么韵脚,没有击鼓的回声,没有什么舞步会破坏我内心的平衡。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写了一首关于舞蹈的诗,其中有这样一个妙句:“他们举起双手要夺取天空的睡眠”。如果我坐下来思考一年,我会发现,若不是某些音节的限制,以及接受或拒绝某些省略,我就必须得醒着或者睡着。女伯爵凯瑟琳可用一段被我放松了的无韵诗来表达感情,这种诗体是根据她的需要而创造的,几乎都不成其为一体了。我认为她是中世纪的人物,因此把她与一般的欧洲运动联系起来。而黛尔德和库胡林,以及爱尔兰传奇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却仍然遗留在鲸鱼的腹中。四、向何处去?年轻的英国诗人抛弃梦想和情感,他们想出了种种使他们与这个或那个政党联合的主张;他们运用一种复杂的心理学,描写的不是象民谣中的那种行动中的人物,而是人物内心的活动,他们都认为他们有权得到人们给予数学家和玄学家的同样密切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yangcana.com/xysls/8405.html
- 上一篇文章: 双阳尹家村母亲身患多发性脊髓炎多年只求
- 下一篇文章: 周四团品7月15日早上,加拿大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