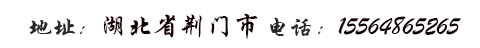老师多年的咳嗽,服中药终于治好了
|
年5月15日的时候,患者程某初诊,男,三十四岁,职业是教师。程某找我看病——咳嗽。我问:“咳了多久?”程某答:“从年开始到现在,满打满算四年。”先不管其他,来了先让他诉苦。程某:“医生啊,我这个咳嗽,真的很惨。”我:“有多惨啊?”程某:“南京看遍医生了——咳咳——还是不好——咳咳——你想啊——咳咳——我一个物理老师——咳咳——在课堂上——咳咳——不能说话——咳咳——一说就咳——咳咳——一说就咳——咳咳——这课我还怎么上啊?——咳咳——学校都把我往后勤安排工作了——咳咳——难道我的职业生涯就此断了?”他看起来确实有点令人同情。咳嗽,病位在肺。咳嗽时,喉咙还痒——风邪。有痰,咳不出来——痰邪。我一看他,体胖,肤色不算白,稍带灰——肥人多痰。我看了下他的舌头,舌淡胖嫩,齿印深,舌表面水滑(饮),舌底瘀血不甚重。舌象总体是一个脾虚挟湿之象。我把了下脉,皮肤冰凉,还湿漉漉的(汗是冷的),浮取不得,用力按下去,脉还挺沉的,力道不是很足,跳得也不快,这是一个阳虚象。然后我就问,大便成形不?他告诉我,不成形,有时一天不止一次。这是脾阳不足。从他的舌和脉、体型和气色上看,都是一个肺脾肾阳气不足之象,挟有风,还有痰。我开了药方:党参、茯苓、白术、炙甘草、法半夏、陈皮、黄芪、防风、干姜、五味子、蜂房、炒苦杏仁。五剂,水煎服。药方中含有六君子汤,它针对脾与痰湿的病机,玉屏风散是针对肺与风的,干姜、五味子、法半夏是针对痰饮的,炒苦杏仁是用来宣肺的,蜂房有温阳补肾之作用,同时还有止咳的作用。年5月20日,二诊。患者反馈咳嗽明显好转。既然有效,守方再服,五剂,每日一剂,水煎服,早晚分服。五剂,水煎服。再加西洋参60克,蛤蚧2对,打粉冲服。年5月26日,三诊。患者反馈说服药粉后,咳嗽加重。这可真是糟了。我有点贪功,想让他快点好,但是没想过他咳了四年后,脏腑太弱了,一下子补这么多,是补不进去的,机体虚不受补。况且西洋参多少还是稍嫌凉,现在也可能不合时宜,用之过早。我想大体思路是不会错的。于是继续守先方,但是不吃药粉。再加巴戟天、麻黄与细辛三味药加强温肾化饮的效果。年6月3日,四诊。上方五剂服完后,四年之咳完全停止了,患者能与我流利地对话。不过患者有个问题,就是颈侧的淋巴结有点肿痛。我一看舌苔,非常白、厚了,这是有湿了,而且湿与药之热结合,化热了。我稍加了两味药,宣肺即能化湿,用枇杷叶;淋巴肿嘛,用点射干就行了;另外再加枳壳,用以理气化痰。年6月9日,五诊。患者基本上不怎么咳了,淋巴也不肿痛了。就是喉咙有痰,难以咳出。我给患者把脉,还是沉,气托不出痰来,或者,痰的出路不够通畅。于是,我在上次的方子上再加了苏梗、旋覆花、百部等能化咽部之痰的药。年6月14日,六诊。患者基本不咳了,喉咙也没有什么痰了。于是再守方五剂。我告诉患者,如果不咳了,就不用再来了。后来,隔了一年再来看其他病时,患者说咳嗽好了。我把这个病例跟大家分享出来,并不是为了说我看病有多厉害,而是想告诉大家其实咳嗽这个病看起来不是个大问题,但是医治起来却要费些周折。古语有:“百病易治、咳嗽难医!”内经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一方面是咳嗽的病因病机比较复杂,医生在诊断的时候必须要统观全局,仔细斟酌,不然辨证容易南辕北辙;另一方面是很多人的咳嗽病其实都是咳嗽刚开始的时候治疗不当、延误治疗而落下的病根;治疗咳嗽中医中药具有明显的优势。而西医治疗咳嗽,主要以镇咳、抗炎、抗感染为主。其主要治疗原理是抑制咳嗽中枢;激素抗病毒、抗生素抗细菌抗炎。即时效果可能很好,但是很容易落下病根,最后转化为慢性支气管炎甚至哮喘,到最后咳嗽就成为了宿疾! 葛根兄 中医执业医师(非科班),自学及跟师学习中医十五年,后毕业于湖南中医药大学。 师承于著名骨伤科专家、原中央保健局保健医吴石华教授,后于江苏省名 老中医、医院名医堂殷明主任门下学习中医儿科、妇科的临床诊疗。 提醒本号旨在推广弘扬中医,结识有缘朋友,志同道合请点赞、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yangcana.com/xyscd/9529.html
- 上一篇文章: 理性防疫不恐慌,正气人体抗击病毒的自身屏
- 下一篇文章: 老一辈传下来的秘方,可信度极高